永遠向世界的一切學習
今年大掃除最大改變大概就是,認清東西在自己死去之後也是丟掉,所以有些東西乾脆提早丟掉的認清現實;如同認清硬碟中收藏的電影如果沒有分享,最後好一點被資源回收,電子零件被提煉「還原」成金屬礦物還可以繼續運用,而「電影」就真的如同自己花時間看過,卻只能留在經驗與記憶中一樣的「虛擬」。
如同以前對買蝦皮也有疑慮,不過現在真的想買,方便就好,以前會堅持盡量不要浪費包裝,現在已釋懷。
如同不買飲料說不想浪費紙杯,被一旁同行友人說,省了一輩子遠遠不及全台灣一天被丟掉的量,我說我知道阿,我稽查過資源回收我怎麼不知道,就當作是一種「修行」吧。修行,幸好嘴我的同伴他還聽得懂。
這種認清還延續著前年上半年很忙下半年沒展覽太閒自修,沒有去駐村的精神游牧,去年展覽到年底之後,今年過年前的展覽延期提前放小假,突然像與世隔絕班地更看清楚廣袤的世界與藝術小世界的關係,以至於圈內很多過於天真爛漫,與人情世故不夠純粹的戀舊,對自己而言在心裡起了一天的漣漪之餘。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離得更遠,但偶爾還是要稍微靠近一下。
發現勢必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而不是什麼未經反芻、故弄玄虛的理論,一如前年自修尼采的體悟(節錄如下)
沒有作為藝術家的任何目的,在當下沒有任何收入,沒有任何補助,沒有任何想要對話的藝術社群。
以如此純粹自由(虛無)的方式(狀態)
生活,如路邊的觀察與思考之間,對自我生命的意義
也許生命經驗苦痛中迴返的提煉、反芻的「自我提升」可被解釋成一種作為不得不成為「藝術家」(幾乎沒任何社會生產力)的,
必須用一種枉顧他人價值判斷(一切價值重估)的,而且相對是不被多數理解(如此摒除俗世的評價與虛榮),一種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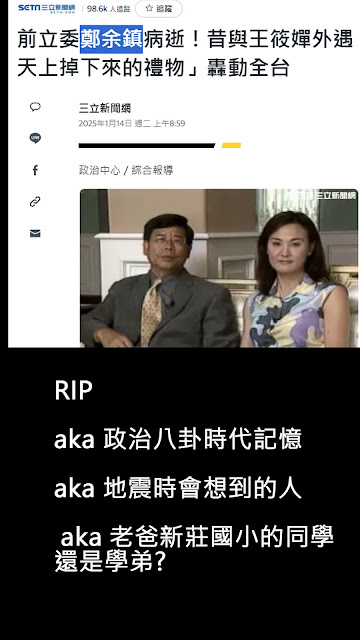
鄭余鎮過世,不是很熟悉台灣政黨歷史,但想起很久以前民進黨 草莽 慓悍 辛辣 很直男 (如:大家有些受不了的老柯?),如同鄭余鎮之後,自己會自動連結到的名字 周伯倫、民進黨「立院三寶」等等 那些距離 蔡英文上任之後引領的文青風 設計感 已十分遙遠, 乃至於 青鳥現場看到許多邏輯與口條很好,又很有禮貌的覺醒青年?,或小草會聯想到科技宅、外送員等等
前天看了黑澤明的《蜘蛛巢城》雖是改編莎翁的《馬克白》,日本版女巫預言與諂惑了接下來兩代的君主,雖然是在講野心與鬥爭,但對於我來說就是俗世的奮鬥,同時也預告了被淘汰的命運。
整體來看,時代性與歷史的意義,就是這樣的吧,或許新一代對於父親年輕的打拼稍有印象,但對於祖父輩的全然陌生,可是或許內容相差無幾,只是風格轉移,有點熟悉又陌生的時間感。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在歷史的不斷推湧的浪潮 前人不得不承認,或妥協當今流行與趨勢,但如同那些當代藝術的現世金字塔底層的三十歲前的年輕人前仆後繼的為理想嘗試奮鬥,多數未果,於是在下個十年又有新的人 新的東西 新的議題 但同時又好像只是不斷重複的輪迴 。
不知為何上週去靜慮藝術觀看《像是隔著一扇窗》- 吳書竺個展,會想到男生— 理性 女生—感性這樣刻版印像,但放在陽剛的競爭社會,又出奇好用的當代概念藝術所強調的「聰明」、策略性,所以哲學後設性的思考是陽剛的嗎?
或是看到「市面上」 乾脆 女性藝術 宣稱著自身女性的特點 (政治藝術)
在想 「虛弱」 要如何宣稱 或者 有必要宣稱嗎? (請老子回答)
因為藝術家不在場無法詢問,作品是不是受到外界影響,現場看到媒材的 混搭 折衷感 。或許是還在摸索的現狀誠實展現(這樣很好),所以反而看到現實影像的理性與感性的手作雕塑裝置的對立。更推測到女性藝術家內心是不是在 當下 邏輯 理性 策略當道的藝術環境中拉扯
有人說男性女性根本假議題, 因為 男性也有女性特徵(反之), 所以 應該是以 「陰性」 「陽剛」 作為區分 如電影《艾諾拉》中反而能以動物性—雌雄的分野與錯置加以解釋,「陽剛」意味爭取、強迫、主動;陰柔代表被動、消極。
但男女天生設定是一種精神分析式,牽制著人們溝通、被看待方式 (帶有一種根本、無法抹去的「後設」)
意思就是作品永遠會不夠純粹,於是要如何更純粹?
永遠向世界學習,如同現場牆上不銹鋼層架泡沫般的爛泥(如上圖;照片源自靜慮藝術FB),此展也提醒自己在意微不足道的「綻放」,如油漆背後的生鏽紋路 不一定要被限制在原本的侷面(侷限的面)。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