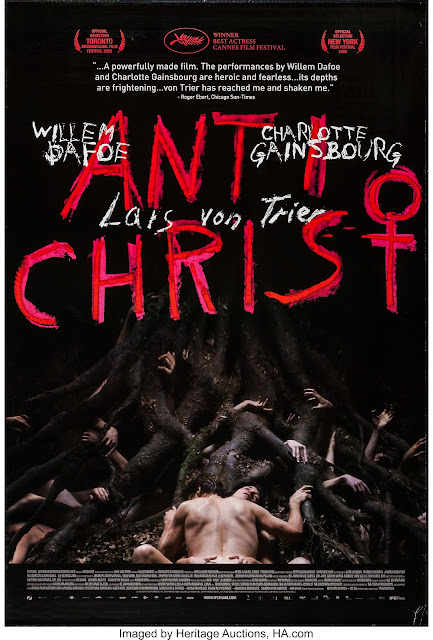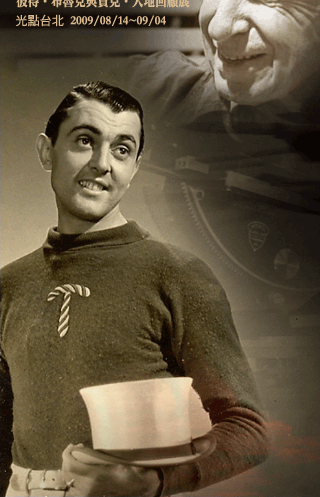你們同情有美嗎?
必須趕快趁有美還沒「變弱」之前,趕快書寫她這一段在「必須」不合邏輯又充滿「在地關懷」式的瘋狂愛情,那個無可救藥的精神性似乎已經能夠達到所謂「藝術的最高位置」。並且同理對照,前些日子游文富淚灑景美人權園區(注意:這邊並無任何嘲諷意味)事件,那個完全捨去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正如同有美在「天下父母心」中,見神殺神、見佛殺佛的「全知」行徑,一個堪稱永恆的至高點。(注意:這邊並無對游文富事件有任何選邊站意見,我是對有美比較有意見) 會想特別書寫下來的最大原因是因為,那天去三媽內用突然驚見老鼠在電視旁邊攀爬,然後電視上「天下父母心」的有美就一直哭說「快救志輝阿阿!!」(見影片第七十八集約52分鐘處),我一邊尋找老鼠到底爬到哪去了,一邊聽到有美在不斷呼喊,手邊卻也沒閒著正在考慮要夾著鴨血還是大腸來吃,我心裡一瞬間卻實有那麼「令人著急」的感覺,但是老闆、店員和隔壁桌的情侶、小家庭依舊十分「順暢」地夾菜,接續著「毫無意外」地頭往上仰看著電視。 時間流動下產生相關持續性的恆常的模式很可能是我關心的議題之一:常常無關情緒化的指涉,一種習慣(在地)情境下,而戲劇「方框」的渲染更顯得如此「無助」地,就是有美失心瘋的哭喊是,或像是片段動人音樂給人的感染,為了繼續(八點檔連續拍到三百集)下去而某種可笑理由的封閉宇宙某種計算公式的溢出。 前一刻在看藝術片,後一秒在看A片,我似乎稍微有抓住了那種屬於當下,一時之間也說不太上來的,例如說,那是一種,社交的呆滯感或說所謂的尷尬,硬要聊又口給,出去玩沒有樂子,不熟裝熟一點點懂就硬掰,也不是說是「興趣不合」,非要說點什麼,兩眼對看只有傻笑,因為不想承認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一種關係:科技來自於人性,討論是「邏輯」和「意義」,人機笑點的梗還有什麼可能,說什麼朱延平的刺陵大爛片神鬼傳奇山之寨版有什麼顯著當代性,想如果不是因為吃了不知道什麼鬼,太嗨造成的失態,或是某種「停頓」,我願意用更「不順暢」來形容,「詩」性被硬生生地打折。 無名正妹相簿或雅虎信箱旁邊的內衣廣告的,被輕易俘虜性别刺點,這邊借用牛俊強的「當我和你老去 」標題:你們同情有美嗎?感性的時間宇宙的理性判斷,藝術的最高位置是建立在相較於他者的日常無感,辦公室的日常,晚上睡覺前上一下網的日常,有美受夠了嗎?另一齣膚淺悲劇而已,或者是我要打的下一則廣告是我偷偷地在員工餐廳看「夜市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