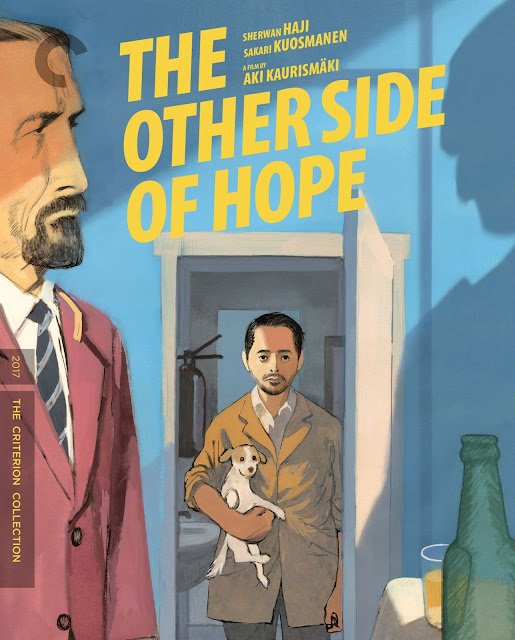她的危險遊戲(Elle)

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巧合,看完「 樓下的房客 」再接續著觀賞「她的危險遊戲」,這兩部某種程度上議題有些接近但看完的感覺卻如此不同,像是拉出東西方看待情慾的方式:一種比較,一種想像,也是一種現狀。 無意分析「樓下的房客」,但還是稍微講一下這部片藉由非常寓言、架空的世界觀,非常不生活的方式,以一種想像的、隱喻的、非常符號的觀看方式起初在尚稱精準的美術與音樂的氣氛建構上在國片當中還算是某種創新,但卻在劇情隨著角色崩壞、大亂鬥之後漸漸顯見深度上的疲軟,甚至已經變得過於「熱血」,以至於那些情慾流動、變態殺人、栽贓嫁禍等等為了彰顯人性黑暗的情節好像變得如此「正向」。正如同任達華激昂地看著監視畫面像是指揮家一樣揮動著雙手,正如同網路上那些類似卡提諾論壇會有的哲學討論區出現的討論標題:「人為什麼需要道德、何不順從自己的慾望就好?」,這類把道德還停留在儒家內部:禮節,忠孝仁愛等等來自於中國文化歷史的規訓,而不是關於人的自由問題,就像是在小學國中時期只是為了反叛老師,不想尊師重道而變得邪惡,但出社會又是另外一回事,這才是我覺得為什麼「樓下的房客」到了中後段如此「熱血」的原因,也算是變種的台式小確幸了。 「別人在上太空,我們還在殺豬公」?好像也不能說「樓下的房客」的基礎偷窺慾望的表達,這樣在國外藝術作品都已經非常老掉牙的方式。反而是要藉由這部片反映出我們的身體感、記憶感。如同上一段所說那樣招喚出熟悉的「校園記憶」、談論情慾的記憶,那應該都視為一種唯一的,而非我們是比較落後保守的,不會當作是一種程度上的差異。 並且依循這樣的身體記憶來看待「她的危險遊戲」裡頭的法國生活感,光是在台灣要闖空門並沒那麼容易,想像為了得到電影中那種強姦的快感還要把鐵窗鋸開這樣大費周章就已經變得搞笑了。如此不太可能發生在台灣的類比情況,更不用裡面最重要呈現出那種,法式的浪漫和自由的人際關係的想像,主角與前夫的聚會呈現出老夫少妻、少夫老妻、偷吃胡搞瞎搞等等種種十分生活化的描寫好像看起來都很正常一樣,但後來才發現其實是荷蘭導演Paul Verhoeven擅長謀殺、血 、暴力、情慾等等作者標記,但在「她的危險遊戲」又如此不張揚地將那些特徵隱藏在角色的情緒、慾望等想像之中,看起來卻是如此法國式寫實感的電影(阿薩亞斯、達頓兄弟)。 在好奇本片是否是為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量身訂做,因為實在太適合她了,活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