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北美館年度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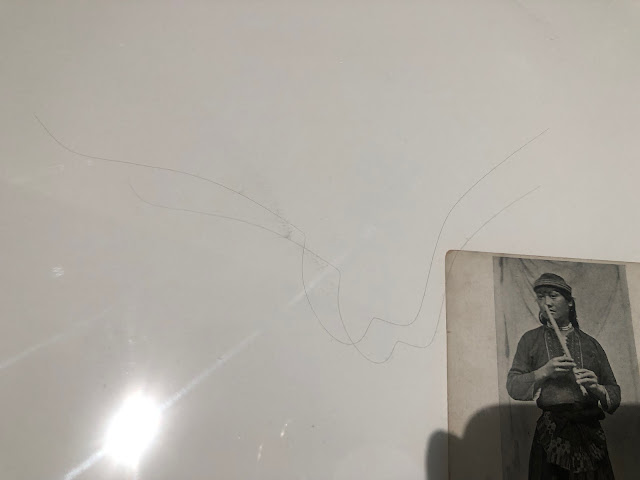
第一次去看,施懿珊去年C-LAB的CREATORS進駐計畫,本來就是朋友,又是「同梯的」對她計畫內容算是很了解,展覽內容覺得依舊文字的知識性大於感受性。 饒加恩,展覽布置算是很不錯,用簡單的方式(並無太誇張的木作)做出空間和作品適當的呈現方式。 並非是產生獨創的作品,而是跟國外(歐洲)當初(日治時期)拍攝台灣原住民的歷史資料的再呈現與再作品化的方式。 張永達,完全不透光過於封閉的展場設計,加上作品以輻射科技感測之名,行酷炫表現之實。看似「最好」(應該說高級感)的展覽呈現,其實是最無聊的。 王耀億,一進去的多頻道錄像一直處於很不錄像裝置的電影播放方式,關鍵應該在於多頻道螢幕的位置處理與聲音太過於劇情性。 孤軍議題的影片很政治正確,手法依舊是紀錄片+實驗片的拍法,且欠缺新意。 旋轉投影機來扣和其他影片關於邊界、遷移的人等被尋找,認清的他者,算是唯一驚喜。 另一個螢幕一次輪播三部電影,個人覺得太硬塞,時間太長來不及看,先離開了。 饒加恩展覽某件作品 第二次去看,施懿珊(火旺教授)親自講解。舉例來說:她把中間技術(臉部追蹤)與中國網民販賣突破技術的假臉部份解釋得很清楚。因為手機與三低影像過於普及,其實對一般來說技術與知識的門檻反而不是像我對新科技很不熱切擁抱的人,往往會會錯估形勢;另外,數位孿生的懲罰形式,其實講簡單的一點就是網路上言語霸凌,如果可以被懲罰、如何被懲罰這件事情,相對網路原住民對他們來說是相當熟悉親切的問題。 王耀億第二次看了他的短片,發現是芝加哥藝術學院畢業的,但怎麼有點像是電影系的感覺。 第三次與火旺教授線上聊天 聊到王耀億的「跨域」的問題(聊天中提及他們布展與開幕時交流,以及去年評審的考量),以及議題取勝,但放到美術館空間因為不熟展現方式,像是把電影院式的現代藝術展現方式直接搬到美術館,像是被抽乾了,就是在電影院直接看電影的意思,兩者沒有差太多,但說真的相較之下美術館設備也那麼好。 提到饒加恩與張永達館內的研究員評價不是很好,前者是後殖民議題做到爛了。後者大概就跟大家的想法差不多,高級的布置方式,但無聊的呈現。饒加恩部分有內幕消息指出說是有更大的心力會放在其他的地方,所以這此展覽比較隨意,不過我是抱持懷疑。 火旺的部分最後幾次這樣看下來,反而會是今年四個展覽中最特別的,雖然布置上如果有另一種面貌處理資訊與知識上的部份 會很不一樣。即使後來發現 火旺教授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