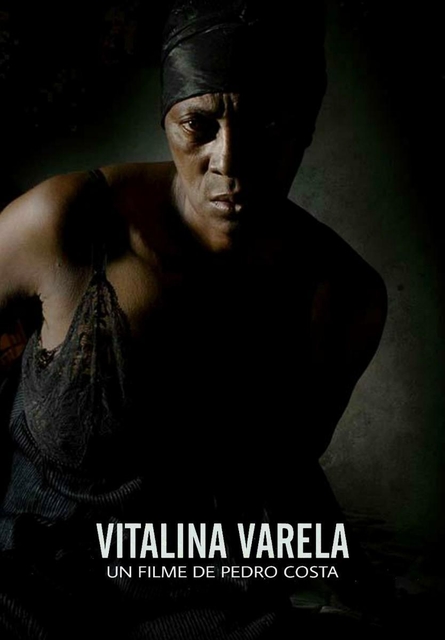想像成為別人的生活
不知為何幾年之後去郵局寄信的時候,依舊會想起很久以前想像著:如果自己是在郵局當臨櫃行員會是怎樣;又如同在台北東區的便利商店,看到中午穿著入時的上班族在排隊結帳,想像著自己也像是他們那樣,跟同事吃完飯後一起去便利商店買飲料跟咖啡的想像。即使那是在現實中如過往雲煙般成為「前任」的正職,那樣已經認清跟同事之間中午買飲料只是想盡力跟大家打成一片的認同,到後來卻在群體垃圾話的語境中感到迷惘。 如同時常看電影,或者紀錄片想像著成為別人的生活,又或者那根本是嚮往某種的自由,就如同三不無時還會想起當稽查員時的陽光午後,自由自在的騎著Ubike,或在街頭中悠閒的散步,沒有身分的賺錢,這樣已經很好了。 也或許是大部分是學生時代所懸欠的想像,想像著少數同學下課之後還在外面外面打工,加油站的大夜班,尤其是在交流道下的四周荒蕪的加油站,如何度過死寂又無聊的漫漫長夜,像是永恆一樣。 『 我好像沒有說過自己對於高中女生的某種感傷情懷,應該是源自於那個好多年前高中時代的(暗)戀愛情愫或根本說遠去的歷史銘刻在高中女生的短裙和開心笑容、大鬧;場域的距離感站在西門町六號出口,原來那就是集體性的青春肉體行為喧囂相對而言的孤獨,穿便服那位先生。 』 - 大眾流行高中女生 (Popular public high school girls) 如同以前對公車號碼後面的的地名,哪裡到哪裡,想像那裡沒聽過好像很遙遠的地方,想像著自己坐公車到了那個的地方。如南港舊庄,後來騎腳踏車登山下山時經過,經過的舊庄公車站,這樣不經意的「相遇」,並想像著居住在舊庄的生活。如同去稽查的時候,到了不同的區域,有時候都會想像住在「這邊」的生活。 就好像是每次在路邊看到快遞在送貨,貨櫃門沒關,就好想跳進去躲起來,於是在黑暗中不知去了何方,想像著等到快遞員重新把門打開之後就好像到了「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