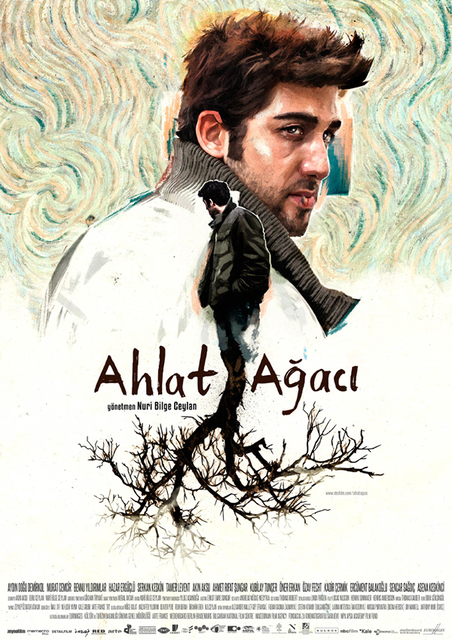鑽進去那個洞裡
朋友M劈頭就問我:「阿是找到工作了沒?」聽了覺得有點奇怪,本來跟朋友是可以開玩笑的,但因為像是被踩到痛處,因此認真了回答起來:「因為過年後要去新加坡展覽,所以過年後再說。」 倒是後來朋友L聽我過年之後要去找工作,說:「你不要去找工作啦,接案錢賺得少,但可以過生活就好啦,反正平常也不需要花甚麼錢。」人生也不一定要賺大錢、幹大事,聽起來有點皈依般虛無,倒是有些共鳴。反正經過樓下工廠的時候也早就習慣被當作從事「自由業」看待,卻總是無法自我感覺良好。看到小我一歲的親戚一直努力地擴展家中公司的業務,中午吃飯有時候會在樓下遇到他往往正在跟客戶熱烈的通話,幸好這樣就可以趁不注意的時候快步離開。 心裡像是羞愧地無地自容,如同那天晚上夢到那位親戚在進行暗殺的行動,眾人面對著牆壁不知道背後有人磨刀霍霍,夢中知道自己會被暗殺,於是我鑽進去那個洞裡,那是每天在看著家裡窗戶外面的鐵皮屋工廠前面一直在施工的排水涵洞,過了一個月都還沒施工好拉著黃色布條禁止進入的洞。 進入了洞裡不是一片漆黑,我像是電影裡由上往下的視角,像是到了一個以前去過的地方,像是城中區的東一排骨飯內部裝潢,或是早就沒落的三重湯城商場, 正是看到眼前有些懷舊意味,又某種的冷清、荒蕪的風景就忽然感到有些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