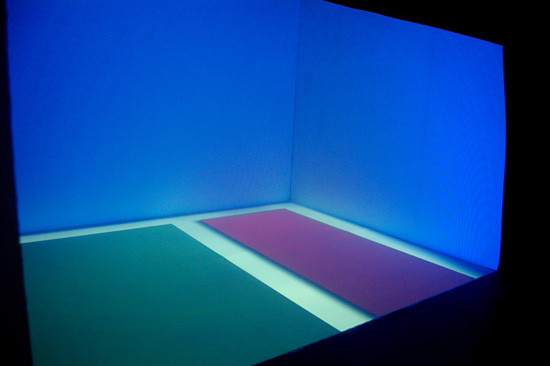把冷漠用在別人對你熱情的地方,把熱情用在別人對你冷漠的地方。
突然收到老爸在對岸生病住院的消息,全家陷入一陣恐慌,而我能做的,就只是幫我媽印台胞證的照片,趕著隔天讓家人用最快的速度去探病。 傷逝與預言,過去的一群朋友們,曾經的一群朋友們(或家人們)。歷史的演變,尚未發生到成為歷史的過程中,從感性眷戀到客觀的歷史名詞,從尚未發生到已經發生。成為遺跡的過程,即便後來老爸病情好轉了,家人不在,空蕩蕩的家中有那麼存在魔幻的一刻,曾經熱鬧又忽然消逝。 這一次生病之後家人開始認真思考年邁的老爸在外面打拼的適切性,但我要說的不是希望跟隨老爸的腳步延續著企業家在外頭打拼的冒險精神,而是現在狀況正是迫切面對人生的現實問題,那個即使在藝術大學的同學瞎聊當中看似可以輕鬆帶過的話題,就是這樣的落差,我的藝術跟現實才得以成立,那個成立的有效性來自於自己不知道哪裡來的無形壓力,總是自問自己好像做得還不夠多,不管是對家裡還是創作,卻也是這樣距離懸殊的兩個極端,對比上課回來的悠閒與家中樓下工廠用力的打拼,無時無刻的暗示,暗自努力在很多人都看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