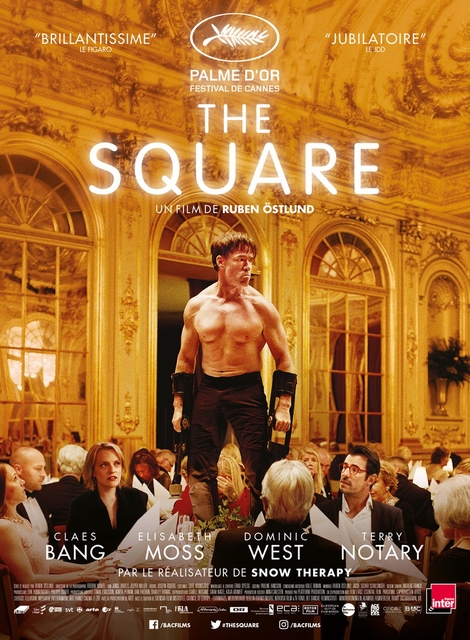黑澤清的末世論

因為昨天已經跑過步今天是禮拜一上班族的憂鬱星期一,開玩笑就算失業在家我也不能閒著,於是隨便去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晃晃好了。準備要去巷口等公車的時候媽媽和附近鄰居在等垃圾車時閒聊好像很開心,一個親戚看到我跟我媽說(我) 要去上班了喔?我媽似是而非的小聲說了對。我想在當下我媽也不方便或不好意思說我離職之後還沒找到工作的事實。這讓我想到「東京奏鳴曲」那個爸爸失業了還要西裝筆挺假裝去上班的日本文化傳統。但在台灣好像可以比較厚臉皮一點,像是我有時候工作時間經過家裡親戚的工廠出入時遇到親戚還是會打聲招呼,卻又好像有些羞愧的料想對方是不是覺得我很閒,或是有去積極找工作了嗎,之類的種種台語說要有「頭路」,想像就是英文ahead要有方向的意思。 從「光明的未來」裡帶有某種西方左派革命理想與日本集體社會意識的對峙,之於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對現實的躁動、反叛,呈現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幻想水母如此美麗佔據著東京市區的河畔,對比著社會化的大人們無聊和醜陋;到了「東京奏鳴曲」那個因為父親失業產生家庭變化,如同在台灣偶爾會聽到在金融風暴之後爸爸失業家道中落,而「東京奏鳴曲」卻用一種溫暖的筆觸,像是被溫柔的殺死的悲劇性。 一直到了近作「散步者的侵略者」在科幻寫實那樣有點好笑的呈現社會身分(外型)與認知意義(內心)的歪斜,前半段除了讚賞黑澤清肯跨出新的敘事類型,並且保有以往過去關心的議題並且更深入的探討。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心不可知,但又必須和其他人溝通的矛盾本質,以及與當下社會身分的規訓與異常身體的姿勢去癱瘓社會的系統:主角身體在被外星人佔據之後,走路像是流浪漢或是某種障礙者與正常人有所區別的狀態,和本來囂張跋扈的廣告公司老闆被抽離言語思考能力之後變成像小孩子一樣把辦公室搗毀。諸如此類在過往社會中被判定失格的廢人卻套用了外星人入侵的科幻情節,三分鐘不,三天就可以把人類都殺死,名正言順的毀滅這個世界吧!?但又想到 Zizek在講傳統左派們可以提供比當下資本主義這樣有點糟糕的世界還要更好的世界嗎?像是回答了「光明的未來」的反叛就只是一種反叛,長大才發現好像不太能改變甚麼,但壓抑變成一種反應,如同我記錄下來早上所發生的事情;如同「散步者的侵略者」這樣藉由外星人入侵,可以理所當然的厭世但好像因此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