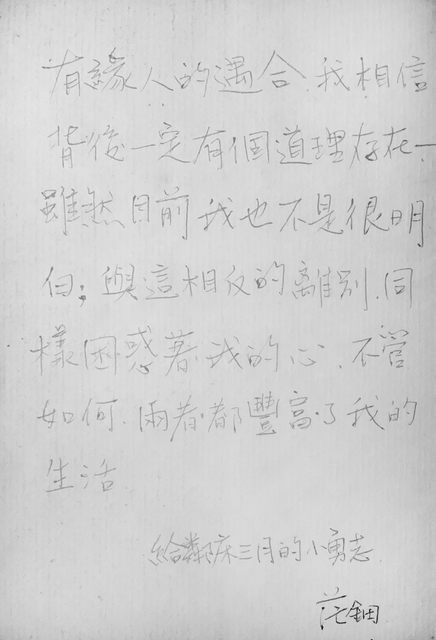看完大佛普拉斯(The Great Buddha+ )的禮拜一

上星期六看完「大佛普拉斯」的滄桑影像感延續到了禮拜一,體制照常繼續的禮拜一。能在上班有公車可以坐並且想事情不就是證明,「若是體制崩壞的話」這樣的假設只能是一種空想。但我也不是一位激進的革命份子,我想是因為電影裡的荒涼破爛喚起自己記憶中的曾經到過的那些廢棄的無人空間。 即將離開的工作,主管說可以開始找工作了,還可以報備去面試。想到了以前自由業時期,沒有星期一到五的節奏感。是不是就如同電影裡面肚才,土豆的時間感。如同以前沒事的時候會去圖書館看書,晚上準備回家的時候對外界環境的陌生。「我在這個世界存在嗎?」心裡曾經有這樣的疑問。確實那樣好像跟人沒有任何關連的加入,離開,就是這一種感覺。對比著電影裡物質匱乏的類遊民,拾荒的街友們,從沒有自由中得到全然的自由,某種方面是毫無牽掛的個體。 那人跟人又有如何定義差異?這也就是為什麼,用新自由主義順暢地理解:人要做什麼就只是一個人的自由,所有的一切都是個人的選擇。那這麼說不就是會被社會學理論反駁那些無法往上爬的人,是階級的壓迫而不是他自由的選擇。但富裕的標準,物質的滿足條件是什麼?爽是因為他自己「覺得」爽,跟別人「認為」他爽或他不爽是不同的思考層次。這就是為什麼信仰上的解釋,比社會學上的批判來得更有趣。 那是背於電影中鋪成的反向思考「苦行」的意義? 關於黃信堯的幽默不必多提,初見這位導演是在「 多格威斯麵 」裡的柯賜海,令人印象深刻的旁白,從英文翻譯成諧音理解台灣美學的虛無,或說虛無的台灣美學。延續到「大佛普拉斯」, 招牌式的自婊式嘲諷感十足, 還想到恆春兮。 因為那天看完「大佛普拉斯」回家公車上一位乘客厭倦車上乘客太多太擠露出嫌惡表情,一付自己可以搭公車就不准別人搭公車的樣子。不禁讓人心想:有能耐就自己開車啊?不是真要他自己開車,因為這樣不太環保。要說的是,從生活上遇到的小事就知道那個認為人的善良天真與階級是不同的事情,我不能因為是遊民就覺得他可憐,當然大部分人有時候會覺得他們可憐。所以片中給出小人物的沒有正義,也就是這部片 最大的問題在於那個陰謀,因為一個兇殺案拉出一個善與惡的劇情,於是就讓人易於切入的這樣有錢很可惡與窮人很慘的利害關係,這樣易於讓人同情的,讓人便宜推斷的階級關係。 但正如我說新自由主義可以自由地闡述個人意見,但千萬要知道這是透過人內在感性地在發表個人意見。於是我看到「大佛普拉斯」影像滄桑感和自己過去遊歷過的場景...